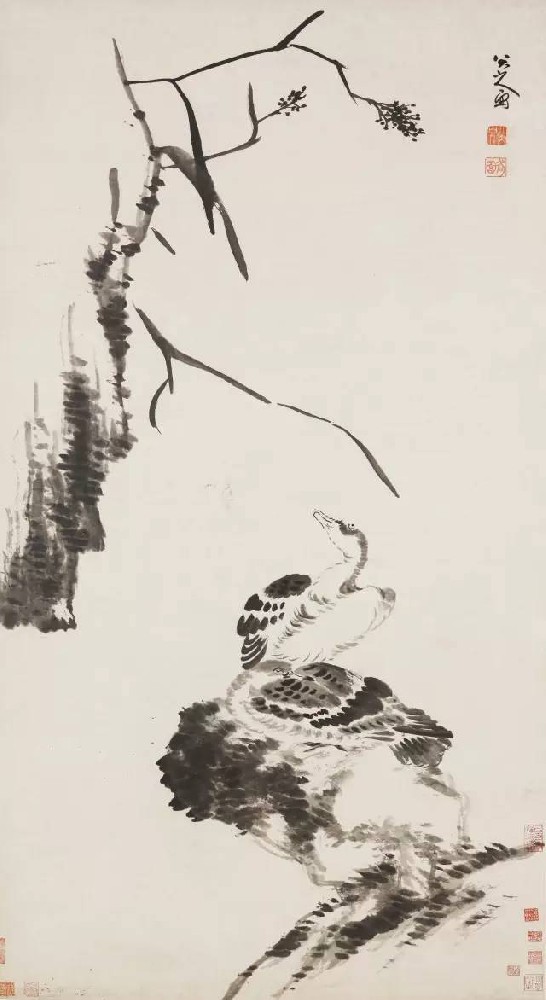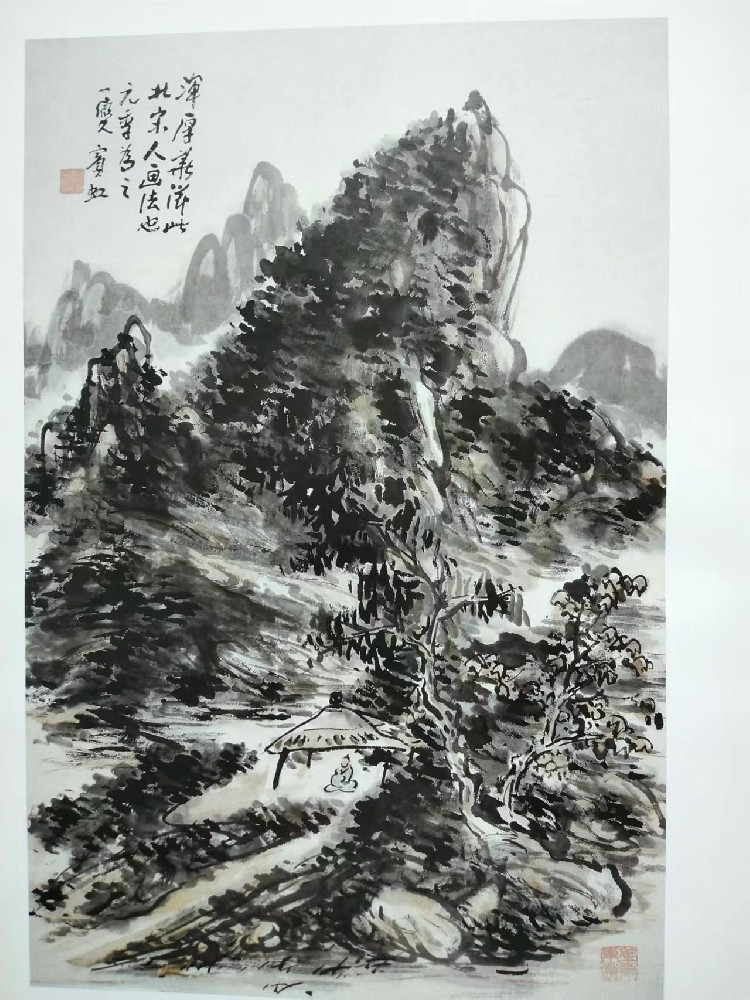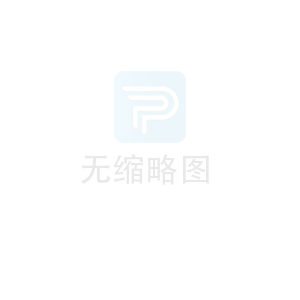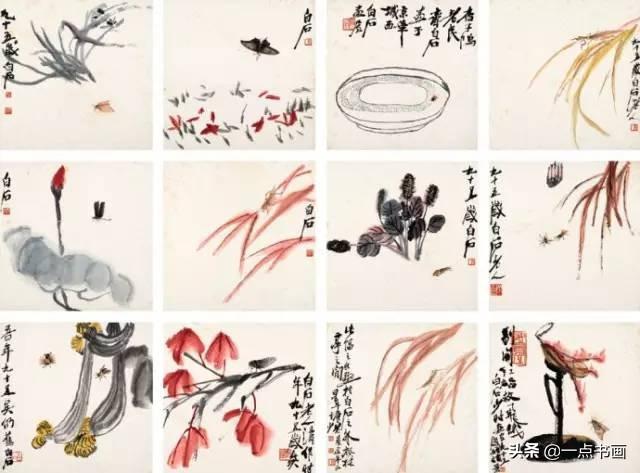六,历史的面容:个人和集体的肖像
历史画可以是历史人物的肖像,也可以是历史事件和场景,或两者的结合。但沈先生主要画历史人物的群体肖像来表现那些历史,或确切地说,表现那些沈先生心目中的真实的历史。
那么,为什么是肖像?这是我的疑问,但未必是一个真的“疑问”,“It is what it is/这样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仔细看过那些画,注视过那一张张早已逝去和被忘却的、仍被颂扬或仍被诅咒的生动的面容,你可能会问” Why is it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两次和沈先生坐在他家的客厅里,沈先生都背对着阳光灿烂的阳台,而笔者则面对着窗外波光粼粼的大海。所以笔者只看到他的一轮“暗影”,只能感到却看不清他镜片后的眼睛——是一种怎样的目光才能洞穿百年,挑选、记住和画出那些成百成千的头像?
但我知道,沈先生的眼光很厉害,他在《自说自画》里记述一位病入膏肓的朋友时说:“死神的颜色是柠檬黄的,它挤满了孙宇的眼睛,从那里直视我。”沈先生在回忆另一个将死之友时,也说道:“他眯起柠檬黄的眼睛,笑眯眯地说……。” 他竟能看到死神的颜色,那么也当能看见面容背后的人的活生生的灵魂。笔者在此,并非意指他有传说中的“天眼”,而毋宁是说:他有观察人的嗜好和能力。至于是因了嗜好才得能力,还是有了能力才生嗜好,可能谁也不清楚,包括他本人。
沈先生说,他的每一个肖像,都是以真实的照片为根据;如果没有见过照片,他绝不会动笔去画。这一原则,让笔者着迷:一,他怎样在真实性第一的基础上融入他的艺术性——一种历史性的自我解读和评判、一种美的视觉性的表现?即历史文献的理性分析、评判和绘画的形象、色彩的表现如何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穿越和融合?二,过去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沈先生的画是彩色的,他凭什么为他们着成现在这样的“色”?在这一过程中,他投入了多少个人的热爱、惋惜、憎恶等等情感?一张张逝去的苍白的脸,在他的笔下一点一点地冒出生气、表情和各种色彩的神色,然后凝结成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地位的符号——一个名字……,在笔者看来,在这一过程中,画家就是一个巫师或魔术师,他将逝去的人招魂到现在,让他们起死回生地接受今人的重新评判。这或许就是强·麦克唐纳说的“乐趣和快感”?或陈丹青说的“癖好”?
沈先生说了一个故事。他原本一直没见过辜鸿铭的照片,不知他的尊容。七十年代后期,偶然在工作单位看到一本1927年的杂志,封面正好有一张辜鸿铭在该年访问朝鲜时拍的照片,且姿势、表情十分生动。他立即翻拍备用。十年后当他开始画《宽容》时,就自然而然地以辜的身影作为构图的起点。他说:“一幅画的构成里往往有一至数个造型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个人物的造型便是此幅母题的关键部分。”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奇妙,在此,沈先生个人的偶然经历与一段过去的既成的历史交汇,并决定了对它的表现。这就吸引了我带着这个故事,再去欣赏这幅画。
展开画面,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侧影,及其一张老去的有点苍白、有点惊愕和不解的脸,——他就是辜鸿铭,一个站在变革关头的反变革斗士。他和左后激进的陈独秀、后中宽厚的蔡元培和前右温和的梁漱溟形成了一种张力。一个在剧变时代的保守人物,居于聚焦的位置,这个构图本身就诠释了宽容的真谛——宽容,就是宽容异见者、少数派、反对派,甚至是宽容“不宽容者”。由此一幅具象的画传达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此,沈先生在历史和艺术的边缘或中间,取得了“左右逢源”的效果。
七,历史不忍“横看”——《革命》、《救亡》、《启蒙》
沈先生在一篇介绍《兄弟阋于墙》——即《革命》、《救亡》、《启蒙》三部曲的文章里说,“这件作品也是‘腰斩’中国二十世纪史,在1936年6月底到1937年6月底这个一年时间里横切下去。”这对笔者来说有两层意思:一,既然是“腰斩”,那就是横切肝胆、脾胃和衷肠——酸甜苦辣咸,五味合一锅;二,纵向的人和事件的历史发展背景,而横向的、当下的、甚至是一瞬的呈现成为主题。
读文字史,即是读一种逝去的、发展的、时间的、纵向的因和果;看历史画,则看到一种空间的场景、横向的关系——无论是在起源点,还是在高潮段、结局处——都是一瞬间的停格。它是生动的、描述性的,而非抽象的、结论性的。所以看历史画,首先是一种对历史的体验,一种印象和想象,而非认识和判断。
比如,笔者在电脑上打开《革命》这幅画卷,看到有苏联人、其他高鼻子的外国人、戴红星帽的中国红军、穿时髦西装、旗袍的其他中国人,我的感觉是:原来革命曾是各式人等的共识和协力,如一种起源时的混沌。再细瞧,亮眼的人物(我的眼)里有托洛茨基、间谍左尔格、宋庆龄、路易艾黎、朱、毛、周,还有蒋介石、东北军王以哲、熊向晖……,甚至还瞥见了盛世才,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曾是兄弟姐妹?曾在一起喝过酒、吃过饭、开过会……。这似颠覆了我的认知,原来革命不是一种胜者的专属特权,而是许多人、包括失败者、甚至“反革命”都可能有的激情。事实也正是这样:一开始都是革命者,革到后来,才革出反革命者和不会成为反革命的永远的革命者。
但是,使笔者一时困惑和着迷的是,1),《革命》中近一百二十多号人物,有名有姓113个,随便挑一个,都是“有头有脸”的历史人物,无论是英雄还是奸雄;另一方面,挑一个凑近了看,不过只是一个男人或女人,可以用一般的审美标准予以评判、加以喜恶的普通人,——附加在其名字上的历史意义、功过荣辱显得不重要了,而他们面容的形状、色彩吸引了我们的关注。即,他们审美意义上的形象,压倒了其伦理上、政治上的是非功过。2),如果再缩小了、放远了看,不管是英雄美人,还是小丑小人,都不过是一群人中的一员,其历史和审美价值都来之于这一特殊的群体。由此,人本身、群体本身不过是一个事件。如果没有中国——1936-1937年这一历史背景,没有“革命”这一主题,那些人物可能都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不会在我们眼前凑成这幅画。那么,个人和群体,历史和某个横切的场景、和当下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我关掉了页面,闭上眼睛,想回忆和总结一下我对这幅画、这段历史的印象……,那些已经读过的有关对这段历史的文字描述、那些带着意义的表音或象形字符,如同一道道细雨,从上古下到近古、从近代下到现代、现代下到今天,不断地演绎、回溯,肯定、否定,清晰、模糊——没完没了,但在这细细密密的“雨帘”中,“淡”出了几具面容:色彩丰润而表情可鉴,比如托洛茨基、季米特洛夫、宋庆龄、无名小红军、周恩来、蒋介石、高岗熊向晖……,笔者不清楚这些面容在我脑中的浮现是审美性的,还是因其背后的意义?但笔者在意识层面的体会是:人、及其个性、面容等,要超过其历史书的评价;人、及其“横切”的共存的关系,要超过其互相之间的分裂、斗争和胜败。把历史横着看——在一点上定格,那么,历史人物都是人,都是无辜的、又是有罪的,也都是兄弟;至于他们的“阋于墙”、他们的功过成败,不过是些枝枝节节、碎碎沫沫。这大概就是历史画给我们带来的观看历史的独特视角和维度。
八,《西班牙 1937》/革命的经典:理想、激情和艺术
画家在2010年下笔画这幅画的时候,革命早已结束了,而且革命基本上被否定了,画家在2007有一个纪录片,就取名《告别革命》。而且,画家本人也将步入老年,任何革命,即使有,也不会和他有什么(肢体)关系了。套用荒诞派剧作家萨缪尔 贝克特的一句台词-——“金色的秋天,如今只剩下金色的头发了”——“理想的革命,如今只剩下理想了”。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头发已没有了,当然金色也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当然理想也没有了。但是,沈先生却在2010-2012年画了这幅画,而且可以说是“颂圣”式的。这是对过去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怀念和致敬,还是对真正的革命的向往?
《西班牙 1937》讲的是那场由全世界的知识精英参加的抗击弗朗哥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内战,或叫革命战争。今天,光看那些参加者的名字,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朝圣”的冲动,诸如毕加索、聂鲁达、乔治·奥威尔、海明威、罗伯特卡帕和他的情人洁达塔罗,电影导演伊文思、医生白求恩等等。如同英国诗人拜伦在1816年去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人的暴动、1824年去参加希腊的民族独立斗争;亦如同伏尼契的“牛虻”——那时还没有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才是革命的本来面目:它只关乎人性、尊严和权利,而非权力。所以《西班牙 1937》,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只为正义,不为权力;那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它只为正义、不为权力;但也是一场理想的、浪漫的和永恒的革命,因为它没产生权力,而是产生了爱情、友谊、思想、文学和艺术。沈先生说,他在嘉兴格罗当红卫兵时,曾想到缅甸去参加革命。笔者在读书时,曾有一个电影剧本风靡当时,名叫《在社会的档案里》,里面的主人公王海南欲偷渡到越南去参加真正的革命,他的书包里放着一本《切·格瓦拉》。剧作者本人原是第一批激进的红卫兵,后来进入反思,遂有《在社会的档案里》及其被禁、被批判。笔者不敢断言,奥威尔未参加西班牙战争,就不会有《动物庄园》和《1984》;毕加索不认同西班牙共和国,就不会有《格尔尼卡》;关键是:他们卷入了西班牙战争,又有了《1984》和《格尔尼卡》。如果说,《格尔尼卡》象征了法西斯的残暴、暗示了革命的必要性,那么《1984》则描写了革命成功后的结局。那么,革命的命运是什么?必得失败了,才能获得意义?必得上当了、后悔了,才能醒悟和反思?
沈先生说: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么,如果沈先生不曾是一个红卫兵,并且从热血到醒悟,他会画《西班牙 1937》吗?沈先生在介绍文里说:“我用一辆超现实主义的汽车代表了西班牙。”“我在画里把天空画得一团漆黑。这一群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登上这架红色战车,一去而不复返,消失在历史的黑洞深处。”
革命者消失了,但是,艺术家诞生了。
九,审美的、艺术的历史话语权
笔者读到过一个故事,说米开朗基罗在教堂画壁画时,一个教堂执事处处同他作对、予以刁难,弄得米氏忍无可忍,就对他说:如果你再同我过不去的话,我就把你的脸作为犹大的脸。执事听了惧怕,就再也不敢放刁,怕他的脸受到人们永世的唾骂。艺术家创作的历史形象,比历史学家评定的历史人物,有时更加具有说服力,并且往往是一锤子定音。再如,《三囯演义》把曹操描述为奸臣,由此至今近700年,虽有众多的史料、史家为他正名,但曹操在人们的心中始终是一个反面角色,并且仍未看到有翻身的可能。
就这一点来说,艺术家及其作品,具有一种评判历史的并不公平的特权。沈先生是很意识到这一点的,他说:“我憎恶把历史艺术化。”因为,艺术化历史有篡改历史的可能,即使做到最好,那也是艺术,与历史没有关系。此时,沈先生是站在历史的一边,去限制艺术表现的特权。但是,他又说过:“那批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乔治·奥威尔、白求恩、毕加索、聂鲁达、海明威/笔者注)真的什么也没有为我们后人留下吗?我想,他们至少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格尔尼卡》。”此时,他显然站在艺术这一边,来总结历史,——他真的是站在历史和艺术的边缘来“艺术”和“历史”,试图在美和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所以我在第二次访问时,问了一个问题:“那么,是否,你认为历史的结局和影响,艺术的,要超过政治的?因为美是永恒的、无是无非的、是超越的、象征的、典型的?”不知为了什么,还未等沈先生回答,我却刹不住,又“连珠炮”似地再续了一个问题:“是否对历史的公正的评判,艺术的要超过历史学的?或艺术之对历史的表现比之文字的要更加丰富和深刻、也更加自由和富于弹性?”
沈先生看着我,看了一会,我不知道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色彩,应该不是柠檬色吧?然后他又看了我一眼,再点了点头,但,只说了一个字:“是。”——一个画家、艺术家的回答方式:形象多于文字。
十,《巴别塔》组画——一个画家的历史的和艺术的雄心
沈先生自己说过,“大型壁画《巴别塔》是我画家生涯的终极之作。”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只知道此画叫《乌托邦》。进入画室,才知道此画是组画——四幅画各占四面墙。依次是《乌托邦》、《英特纳雄奈尔》……,因另两幅还未成形,故,暂卖一个关子。
站在沈先生高达八米的画室里,要看直耸而达天花板的《乌托邦》,必须仰视,而这一姿势,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我问沈先生:“您的《乌托邦》从什么时候、从谁画起?”沈先生仰着头说:“柏拉图。”我再仰仰了身体,看到《乌托邦》的顶端,站着几个披着布袍的古人,神情严肃地想着什么。柏拉图写了一部书,题名就叫《理想国》。据说这是一本仅次于《圣经》的被阅读和引用的书。记得《理想国》里有一句经典名言:“人生的态度是: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而这,在冥冥之中正印证了人类的一部乌托邦史:沈先生画室的四壁组画——《乌托邦》代表了最好的愿望,《英特纳雄奈尔》则是最大的努力,其他未成形的两面,是最坏的结果?那么,这四面组画的总称是什么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就问了一句。沈先生冷冷地说:《巴别塔》。
“巴别塔!”当时我听了,心中不觉一个格楞——巴别塔、又叫通天塔,是犹太人圣经《旧约·创世纪》里的故事: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但是耶和华降临看到了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都是一样的人,说着同一种语言,如今他们既然能做起这事,以后他们想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他们也就停止建造那座城。】
巴别塔的造不成:一是因为人的野心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想以肉身做成通天的神迹;二是人的“同心合力”状况,仅仅系于说同一种语言这一脆弱的纽带上。上帝只要弄乱这一统一的语言,人,便人心四散,通天塔也就一夜轰塌。
高耸入云、万众一心,是一个至美的理想,但谁来领导这一工程呢?一些人能领导同样的另一些人来“通天”吗?一种理想如果没有一个界限、限制在人力之内,那么任何一种理想不仅实现不了,而且还会走向它的反面。
半年后,当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原本仅是素描的第二面壁画《英特纳雄奈尔》已大多着了色,且色彩斑斓,你能看到、甚至呼吸到沈先生在尽力地画着那些曾经“尽最大的努力”的人们。
我突然想到,巴别塔是能够造起来的,但不是政客、将军、富豪和民众,而是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们,因为他们不使用文字语言,而是使用无需学习、记忆、一看就懂的形象的“自然语言”,所以,上帝无法弄乱它们。人们可以在美的主导下,不为利益、名声、是非,造起一座“巴别塔”来通天。
十一,尾声
第二次访问告别时,还是下午时光,初夏的阳光已开始灼热。沈先生和王兰老师一直把我们送到园外,目送我们开车调头、离去。从后视镜里望一眼他们渐远、渐小的身影,我分明看到:他们并非是站在历史和艺术的边缘,而是站在历史和艺术的中间;并且还站在历史经度和现实、场景、当下、画框等空间纬度的交叉点上。
不一会,他们的身影就看不见了,但还能看见那幢房子、那间画室的一角。但是,谁又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幅颂圣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会与这幢房子、它的八米高的画室发生因果关系;而画室里正在生成一幅反思的《巴别塔》。如此,从《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到《巴别塔》,他们的关系既是Causal/因果的(一种可推论的关系),又是Casual/随机的(一种偶然的、不可测的关系),难道说,是上帝弄乱了它们的关系……
编辑:收藏狗
上一篇:沈嘉蔚 Jiawei Shen | 在历史与艺术的边缘
下一篇:没有了!